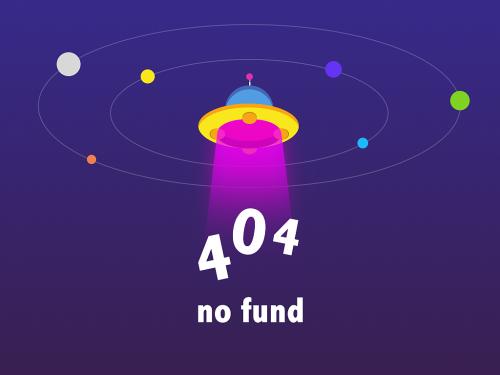摘要:“野生动物”(wild animal)一词不止在我国, 在全球的英语使用者中也有不同的含义。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国内法和国际法背景下的定义和适用范围, 结合人类对动物繁殖和生活条件的控制情况, 本文提出了“野生动物”的二维概念框架, 梳理了动物从“野生”到“驯化”的12个连续状态。以下状态应被视为野生动物: 未经中长期人工选择的动物类群, (1)其在荒野自然或人工环境如城市或乡村中自由生存繁殖, 无论是否存在人工投喂、经救护或辅助生殖后被放归的个体; (2)被捕捉圈养在人工环境中生活或在圈养条件下出生的个体; (3)直系血亲(可参考《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解释为世系前四代)仍有野外来源的人工繁育后代; (4)放生、逃逸或引入到自然环境中的人工繁育个体。在野生动物物种保护的目标和语境之下, 经过长期人工选择的驯化动物, 无论其是否在人类控制下生活, 如家养猫狗、家禽家畜或模式实验动物, 以及流浪猫狗、放生禽畜和野化家养动物等都不是“野生动物”。但对于一些经过一定程度的人工选择, 所处人类控制情况和对野外种群的影响各异 (如经过多代人工繁育的驯养动物、因人类活动导致的外来动物等), 其是否需被作为野生动物管理, 则需要根据生态安全、物种管理, 立法目标等特别设定监管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对象可以考虑为:受到人类威胁濒临灭绝的, 或者具有重要生态作用的野生动物物种, 其状态可不限于在野外还是人工控制条件下。其他动物的管理, 可根据遗传资源保护、疫病防控、动物福利和生态安全等需要, 另外设立《动物福利法》《生物安全法》等, 并和已有的法律法规如《动物防疫法》《渔业法》等做好衔接。本文还就《野生动物保护法 》可能采用的“野生动物”定义提出建议。
关键词: 野生动物;二维概念框架;野生动物保护法
2003年, 为应对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暴发, 当时的国家林业局和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文, 紧急通知立即停止野生动物市场经营活动。但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所适用的范围和林业部门所监管的目标与人们从字面上理解的野生动物即“生活在野外的非家养动物”具有很大差别。因此引发了公众对通知所涉及“野生动物”范围的讨论, 建议必须在法律上给“野生动物”以明确的定义(蒋志刚, 2003)。2020年世界范围内暴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由于其病毒可能源自野生动物, 引发了人们对2016年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适用范围的大讨论, 再次引发对“野生动物”这个常用词汇做出准确定义的呼吁。定义“野”(wild)或“非野”(non-wild)不只是个理论问题, 而且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野生生物”、“野生动植物”、“野生来源”这些概念存在着相对性, 在定义时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周志华和蒋志刚, 2004)。很多国际自然保护协议、国家法律, 包括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iucn red list)都没有对“野生”给出准确的定义(mallon& price, 2013)。为确定“野生动物”概念的理论基础, 本文梳理了部分英语国家、我国香港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文件、法律、法规, 参考了其中与“野生动物”定义有关的术语, 提取了“野生动物”定义的关键信息, 并根据对动物人工选择和干预控制的强度, 提出了“野生动物”的一个二维概念框架, 解释现实中动物所处的不同状态, 揭示这些状态之间的连续性和差异, 提示不同法律规定适用背景, 不同操控意图、规范和语境下应考虑的“野生动物”定义, 并根据现实情况, 就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的法律框架提出修订建议。在我国, “野生动物”曾对应翻译为“wildlife”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法制局, 1991; 马建章等, 2004), 在概念上被认为有广义和狭义两类: 广义的概念包括了自然界所有自由栖息的动物种类, 狭义的概念因时间和地区而变化(宋延龄,1994)。以下为一些国际组织、协议和不同国家、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英文法条中与“野生动物”(wild animal)相关的英文术语及其解释, 包括wildlife、animal、wild fauna、wild population、domestic/ domesticated和captivity等(box 1)。可以看出,相关术语的表述和适用范围因各自法律的立法目的而有所不同。各个国家的野生动物管理和保护法规均从自身的传统需求和法律目标出发, 覆盖动物界的不同类群, 并有不同的限定条件(box 1)。一般地, 术语确定适用生物类群的方式分三种: (1)采用其他词汇做出描述或解释, 即“定义法”; (2)举例该术语所涵盖的类群, 即“列举法”; (3)列出该术语不涵盖的类群, 即“排除法”。各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对“野生”的表述具有不同的限定条件, 主要涉及: 是否属于或者存在于自然中, 是否包括处在圈养和人类控制条件下的群体, 是否包括驯化动物的野化群体等。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定义看, 驯化动物和野生动物并不直接对应。前者强调经过很多世代, 繁殖和饲养受到人类控制; 后者要求生活不受人类直接监管或控制且表型未受到人工选择的影响。然而, 新兴的宠物产业和动物特种养殖业, 有可能只经过几个世代的遗传操作, 就能得到表型、基因频率与野外种群不尽相同的群体。《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将动物和植物以物种(亚种或种群)的形式列入附录。对一些特定动物物种, cites附录在其拉丁名后添加注释来标明其家养型(domesticated form)除外, 如狼(canis lupus)的家养型即狗(c. l. familiaris)和澳洲野狗(c. l. dingo)除外; 又如猫科动物所有种的家养型标本(如家猫或孟加拉系宠物猫)除外。此外, cites公约在附录中还排除了家养大额牛(bos frontalis)、家水牛(bubalus bubalis)、家牦牛(bos grunniens)、家驴(equus asinus)、家山羊(capra hircus aegagrus)和家养型毛丝鼠属的所有种(chinchillaspp.)。而对于新兴养殖产业的一些动物, 无论其表型或基因频率与野生个体如何不同, 都未排除其特定品系。但是, 对于整目列入的鹦鹉, 则通过注释排除了人工繁育动物早已成功占领市场的4个物种, 即桃脸牡丹鹦鹉(agapornis roseicollis)、虎皮鹦鹉(melopsittacus undulates)、鸡尾鹦鹉(nymphicushollandicus)和红领绿鹦鹉(psittacula kramer)。
由此可见, 在讨论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条款适用范围时, 如何定义从“野生”到“驯化”的不同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野生动物的定义和概念的适用性与人们对动物的“野性”判断有关。动物的“野性”可以从动物所处的位置、是否驯服、是否发生了本质性改变三个方面来描述(palmer, 2011)。其中的本质性改变即遗传组成发生了变化, 可以理解为驯化。定义驯化时还要考虑到动物群体的连续变化过程, 如在人类控制下野生动物经历了圈养、驯养再到驯化, 而驯化动物在逃离人类控制下, 又可以从流浪变为野化(décory, 2019)。无论是以食用为目的还是对如猫和狗的驯化, 数千代的人工选择提高了动物对人类存在的耐受力(driscoll et al,2009)。俄罗斯(原苏联)科学家通过银狐(vulpes vulpes)驯化实验发现, 人工选择超过50多代后, 可以得到驯化动物(belyaevet al, 1985; kukekova et al, 2018)。人工选择是人类有意识地对种群的性状或性状组合进行筛选。与自然选择不同, 人工选择是以生存和繁殖为筛选标准, 而非由整个基因型的适应度所决定(futuyma, 2016)。在野生动物物种的管理和保护方面, 除进行人工选择外, 人类的干预水平也是连续的。对动物不同水平的干预, 可使其种群实现自我维持, 或依赖保护、轻度管理、集中管理或圈养繁育, 并达到物种保护目标(redford et al, 2011)。人类对大型脊椎动物的管理干预措施可以从空间、疾病控制、被捕食风险、食物及水资源的获得以及繁殖等六个与脊椎动物的演化和生态动力学相关的属性来评估, 继而可用于评估种群的“野性”(childet al, 2019)。参照以上定义和研究, 从物种保护和管理的角度出发, 我们考察了野生动物从野外种群到被捕捉、圈养到成为驯化动物的一系列过程, 发现可能存在连续的12种状态:(1) 狭义野生动物。即在海洋、河流、森林、荒野等自然环境中自由生活,群体未经人工选择, 个体不受人类主动操控的动物, 也是最基本意义上的野生动物。(2)城市乡村野生动物。当地球进入人类世后, 自然环境或多或少受到人类活动改造。在城市和乡村的绿地、农田中, 也有很多自由生活的动物, 它们的生活史基本不受人类控制, 但可能会因人类建造的环境而容易获得食物、住所, 也可能会受到农药、建筑、车辆等人造物品的直接或间接影响。(3)救护和辅助生殖放归/人工投喂的野生动物。对某些生活在自然中的动物, 人类会采取一定的管理控制措施, 作用于其生活史中的短暂阶段, 但不刻意采用人工选择筛选动物个体。如对一些动物的野外种群在其食物贫乏期为它们提供补充饲料或民众随意自发投喂, 救治受伤动物使其获得在野外生存的能力后放归, 以及卵、蛋或繁殖体(配子)源自野外、但在人工条件下出生或者野外出生的幼体饲养到亚成体阶段后释放回归野外。一些两栖爬行动物卵、蛋的自然孵化率与幼体的存活率相对很低, 辅助生殖回归的操作有助于恢复野外种群。(4)被捕捉圈养的野生动物。出生在野外,因科学研究、育种、展示和宠物等各种人类需求被捕捉后饲养在人工环境下的野生动物, 其无论在人工环境下生活多久, 都源于野外。(5)圈养出生的动物。指卵、蛋或者繁殖体(配子)源于野外但在人工条件下出生, 或者亲本来自野外而在人工控制条件下交配产生后代。另有一些人工繁育群体会因长期近交, 其生存力、繁殖力下降, 需要从野外引入个体补充种源。这些动物即为子一代, 在本文概念中应属于野生动物。(6)养殖与野生的自然杂交动物。释放或逃逸的人工繁育个体在野外与原产地分布的野外种群杂交产生的后代。已有研究表明, 诸如大西洋鲑(salmo salar), 或加利福尼亚钝口螈(ambystoma californiense)的人工繁育个体与野外种群的自然杂交影响了它们野外种群的保护(hindar et al, 2006; fitzpatrick & shaffer, 2007)。从物种保护的角度考虑, 为防止释放养殖大鲵(andrias davidianus)与野外种群杂交造成负面影响, 应开展遗传评估(yan et al, 2018)。(7)放生/逃逸/引入动物。在人工控制条件下繁育的野生动物物种在种群增殖后开展原产地野外重引入的动物, 如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和野马(equus ferus); 渔业部门放流到自然/半自然水域的人工繁育的水生动物; 部分民间放生的人工繁育动物, 及人工繁育逃逸到野外存活的动物。(8)人工繁育子二代及其后代。在这一状态类别上, 《野生动物保护法》(2016年修订版)和cites公约对标本来源的要求类似, 即在人类控制条件下已经繁育到子二代及以上。为区别驯养动物, 其直系血亲可能还有野外来源。cites公约将直系血亲解释为世系的前四代(cites conf. 10.17 (rev. cop14))。(9)驯养动物。经过一定时期的人工繁育,已经形成稳定的人工种群, 直系血亲中无野外来源, 但人工选择的时间还不够长, 不被认为是驯化动物。一些动物因人类对特定表型的需求(如宠物、皮张)可能快速选育出品种, 但也有不少繁育群体在表型和基因频率与野外种群差异不显著, 或者在行为上没有显著的变化(kukekova et al, 2018)。如目前人工饲养的梅花鹿(cervus nippon)、马鹿(c. elaphus)、貉(nyctereutes procyonoides)等, 及部分用于科学研究的实验动物, 如食蟹猴(macaca fascicularis)、雪貂(mustela pulourius)。这类状态相对复杂, 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野生动物, 但因存在对野外种群或相似物种的可能影响, 宜参考cites公约的物种列入相似性原则、预防性措施和合法来源判定操作, 采用证书管理、注册机制和公开数据库等可追溯系统监管。(10)外来动物。源自野外种群或人工种群, 由人类有意或无意携带到一个新的生态系统中, 在自然环境中建立了可自我维持种群的动物。如南欧的和尚鹦鹉(myiopsitta monachus)种群已经开始从城市和乡村往自然保护区扩散(postigoet al, 2019); 我国南方一些自然水域已有牛蛙(lithobates catesbei¬anaus)(bai et al, 2012)、红耳龟(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 (xu etal, 2012)等外来物种建立入侵种群; 新西兰引入的一些狩猎动物(如大型鹿类等草食哺乳动物, latham et al, 2020)、欧亚大陆引入的美洲皮毛动物(如麝鼠(ondatra zibethicus, bos et al, 2019)等, 它们在自然中也已建立种群, 这些种群会对原生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带来负面影响。但是, 如曾被作为宠物进行贸易的濒危物种小葵花鹦鹉(cacatua sulphurea), 逃逸后在香港建立了野化种群, 它们也可能成为濒危物种的异地保护种群(gibson & yong,2017)。(11)流浪猫狗/放生禽畜/野化家养动物。即离开人类控制、在自然中生存繁育不受人类控制的驯化动物。如高原地区被遗弃的流浪狗、自然水域放生的家鱼, 或已经野化的澳洲野狗等, 这些进入到自然的驯养动物可能对野生动物带来负面影响。(12)驯化动物/模式动物。经过人类历史长期驯化但仍生活在人类控制条件之下的动物, 最常见的如家猫、狗、马、家驴、家牛、山羊、绵羊、家猪、鸡、鸭、鹅、家鸽、家蚕等; 在科学研究的强人工选择下, 近代已经形成一些实验模式动物类群, 用于对生物演化、遗传发育或人类疾病开展研究, 如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斑马鱼(danio rerio)、非洲爪蟾(xenopus laevis)、大鼠(rattus norvegicus)、小鼠(mus musculus)等。这12种类型如果从人类控制管理干预的强度和人工选择时间长短这两个维度的连续变化来描述, 属于3种不同的人类管理控制强度, 以及4个不同的人工选择阶段, 可用下图来描绘动物的“野性”(图1)。fig. 1 the two-dimensional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wild animal”第1到第8类无论其是否处在自然环境中都被视为野生动物, 第11和12类是经过强人工选择的动物, 无论所处什么位置都不是野生动物。在第9到10类中, 由于经过一定程度的人工选择,所处人类控制情况和对野外种群的影响各异, 其是否应被作为野生动物管理则需要根据管理和保护的目标设定范围。
人类有意无意将动物置于一些特定的状态中, 有些人类活动有一定负面影响, 如从野外捕捉个体、捡拾卵蛋、随意放生或造成外来动物入侵; 有些被认为有助于野外种群恢复, 如将人工孵化育幼后的亚成体放归、将人工繁育后代放归野外的重引入项目或增殖放流; 还有一些对野外种群的影响以间接为主, 如近百年来兴起的特种养殖等, 其中绝大多数都应该被纳入法律监管和保护的范围。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因“野生动物”术语定义
而产生的问题
《野生动物保护法》(2016年修订版)在第一章“总则”的第二条第一款中阐述了法律适用的地域范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的其他海域”; 第二款规定保护的物种对象是“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陆生三有)”; 物质属性是“本法规定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是指野生动物的整体(含卵、蛋)、部分及其衍生物”; 但没有对“野生动物”做出规定。这与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一版的描述具有一定差别。第一版第一章“总则”第二条第三款标明了“本法各条款所提野生动物, 均系指前款规定的受保护的野生动物”, 即明确了野生动物就是两个名录: “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原陆生三有)”中的动物。比较而言, 反而是《野生动物保护法》(2016年修订版)在修订时删除了“野生动物”一词的术语限定。这一删除直接影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2016年修订版)后续一些条款的适用范围。如: 第三条第一款“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第三章野生动物管理相关条款中所有涉及非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活动, 包括妨碍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猎捕及其工具、出售、利用、运输、从境外引进、释放活体和检疫证明等。 没有“野生动物”术语限定的《野生动物保护法》(2016年修订版), 从字面意义上来看, 理应将这些条款适用于动物界的所有动物。从资源的归属和从境外引进两个条款角度观察, 将法律适用于所有“野生动物”看似具有合理性, 比如对未列入任何名录的新物种和新发现, 其资源归属也明确应属于国家。而且各主管部门也在依法审批非国家重点保护名录和非公约附录所列的境外引进野生动物。
但涉及妨碍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和猎捕等人类活动时, 如果根据以上条款的推及, 则相关管理活动将无限扩大适用范围, 波及所有“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包括苍蝇、蚊子等。当然人们从未据此实施过。反之, 如果《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的“野生动物”只限定国家重点、陆生三有和地方重点, 则其他非保护野生动物的归属以及管理则存在不确定性。综上, 模糊不加限定的术语, 必然造成人们对法律条款理解上的分歧和执行上的困难。我国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承担着“保护野生动物, 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立法目标。参照前述“野生动物”的概念框架, 第1到第10类的动物状态与野外种群的存续相关, 应作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完成立法目标需要保护和监管的动物。在此目标之下,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通过设置分级的名录, 将保护和管理限定在部分物种, 而不是所有动物类群。在此框架和立法目标下, 必须在法条中明确被监管动物的状态, 并限定条款的适用范围。因此, 结合1988年的表述, 参考前述汇总的术语和概念框架, 我们建议将《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一章“总则”第二条第三款“本法规定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是指野生动物的整体(含卵、蛋)、部分及其衍生物。”修订为: “本法各条款所提野生动物, 均系指前款规定中所列物种在自然、半自然和人工控制条件下孵化、生长或繁殖的所有活的或死的个体和卵, 且包括其任何部分、产品及衍生物。” 明确概括现有法条的适用范围。在此定义下, 第三款的前款需排除被归为第11–12类的动物, 但对第9类“人工繁育已成熟, 无需依赖野生血缘的受保护物种的人工种群”, 可考虑采用证书、标记和注册开展溯源管理。为避免第10类动物的影响, 涉及从境外引进非原产动物物种, 以及向自然释放非原产动物活体的, 应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中考虑监管, 并适用其他相关法律加强监管, 如《环境法》《动物检疫法》《生物安全法》等。在2020年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暴发后, 禁止食用野生动物, 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专家学者建议尽快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 对所有野生动物物种实行普遍保护, 并将已经成为《动物防疫法》《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立法目标的公共卫生安全写入《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目标。但通过分析发现, 现有法律条款难以通过简单的修订、添加定义和扩大保护范围来达到既要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又要普遍保护野生动物, 还要维护人类公共卫生安全的需求。在新的立法目标出现后, 需要革新野生动物所涉法律的整体框架。野生动物各类群在栖息地类型、生态功能、生活史以及动物与人的关系上截然不同。各类群的地理分布、物种丰富度、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程度和受威胁因素也各有差异。与此同时, 考虑到我国的珍贵、濒危野生植物保护尚缺乏法律可遵照, 本文建议可将现有《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目标/对象和管理目标/对象拆分。设立《濒危物种保护法》, 保护受到人类活动威胁而濒临灭绝的野生生物物种, 包括动物界、植物界和大型真菌等, 出台《国家重点保护濒危物种名录》, 并及时更新。其法律可参考美国《濒危物种保护法案》《加拿大野生生物法案》或印度《野生生物保护法案》的管理目标和框架, 并与一些国际协议如《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国际湿地公约》等相接轨。对于未受到《濒危物种保护法》保护和管理, 未列入《国家重点保护濒危物种名录》的1–10类的“野生动物”, 及11、12类驯化动物的管理, 可根据遗传资源管理、疫病防疫、动物福利和生态安全等需要, 另外新设立《动物福利法》和《生物安全法》等, 结合现有《渔业法》《动物防疫法》《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 做好相关条款的修订衔接, 解决相关问题。
来源: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